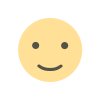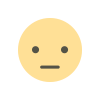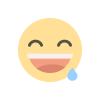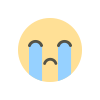我学会了说不,不在乎别人怎么想:为什么要花这么长时间? |艾玛布洛克斯
我想做一些我知道会惹恼人们的事情。这是正确的做法;我对这个事实深信不疑。我还坚信,在用于强加笨拙决定的语言中,我“完全有权”这样做。如果我做了这件特别的事情,它会让我的生活更轻松,但也会导致别人的反对。我可以做到这一点,我告诉自己。实际上,不,我不能。等一下,是的,我可以!等等,没有。哦!看在上帝的份上。好的,我明天再做。
出于某种原因,今年夏天,我经常看到这种特殊的动态。我住在美国,但我的社会群体主要由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主导,我怀疑他们比具有某些自信的美国人更难相处。我认识的大多数美国人可以改变他们对某事的看法,或者完全否认它,而不会拖着自己穿过内部海豹突击队式的障碍课程。我认识的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尤其是但不限于女性——发现几乎不可能做出明确的决定,因为他们知道这会导致他人的愤怒或失望。
一些细节:一位东海岸的朋友,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场婚礼上说“是”后,当她的情况发生变化时想要退出。另一位与即将到来的租户打交道的朋友想告诉他们,他们在最后一刻要求搬家的要求是不合理的。还有我自己的情况,我想把我的孩子从他们不喜欢的夏令营中带走,我知道组织者会认为这是“放弃”。在每种情况下,交换另一端的人是陌生人还是朋友都无关紧要。我们三个人同样不愿让他们难过。
这种情况当然与我们都害怕被讨厌,以及我们有多少放手有关逃避它。我与人建立了完整的关系,只是为了避免拒绝他们的尴尬。我做了你不应该做的事情:说是,后悔,回来说不,遇到阻力,吓坏了,说“其实,别担心,没关系”。这带来了最糟糕的结果:没有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同时看起来像个摇摇晃晃的混蛋。
如果我现在觉得自己超越了那个,陪审团仍然出去。但早期迹象是好的,可能部分是因为大流行。在两年没有经常旅行或外出之后,我们中的许多人对邀请和机会的反应与以前不同。期望发生了变化。计划已经改变。我们都习惯了沮丧和失望。在那里的某个地方,说“不”变得更容易了。鉴于所有这些,现在是重置硬边界的好时机。
我怀疑我愿意做看似困难的事情并不是年龄的函数。我没有时间或精力去建立关于别人讨厌我的奢侈幻想。我们假设别人比我们更脆弱;一次失望就会打破他们。我们也高估了我们每个人在他人想象中的位置,甚至在我们亲密的朋友和家人中。人有生命。他们和我们一样痴迷于自己。不参加朋友的婚礼,因为这意味着错过更大的优先事项,这是一个完全合理的决定。如果新娘不高兴,她会克服的。
所以这是我的新奇之处:在你说或做你害怕做的事情之前,你必须先坐下来辐射的不适。你必须尊重对方生气的权利,承认它是你行为的代价,并假设它会比你对它的怪异焦虑快得多。你必须相信结果——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你认为这是最好的——值得一些不适。很好。
我让我的孩子们退出了夏令营。组织者把我吓坏了。没有人死亡。你去吧。我今年 46 岁,最后——终于——想到“但如果他们生我的气怎么办?”可能会停止在我的决策中考虑这么多因素。

我想做一些我知道会惹恼人们的事情。这是正确的做法;我对这个事实深信不疑。我还坚信,在用于强加笨拙决定的语言中,我“完全有权”这样做。如果我做了这件特别的事情,它会让我的生活更轻松,但也会导致别人的反对。我可以做到这一点,我告诉自己。实际上,不,我不能。等一下,是的,我可以!等等,没有。哦!看在上帝的份上。好的,我明天再做。
出于某种原因,今年夏天,我经常看到这种特殊的动态。我住在美国,但我的社会群体主要由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主导,我怀疑他们比具有某些自信的美国人更难相处。我认识的大多数美国人可以改变他们对某事的看法,或者完全否认它,而不会拖着自己穿过内部海豹突击队式的障碍课程。我认识的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尤其是但不限于女性——发现几乎不可能做出明确的决定,因为他们知道这会导致他人的愤怒或失望。
一些细节:一位东海岸的朋友,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场婚礼上说“是”后,当她的情况发生变化时想要退出。另一位与即将到来的租户打交道的朋友想告诉他们,他们在最后一刻要求搬家的要求是不合理的。还有我自己的情况,我想把我的孩子从他们不喜欢的夏令营中带走,我知道组织者会认为这是“放弃”。在每种情况下,交换另一端的人是陌生人还是朋友都无关紧要。我们三个人同样不愿让他们难过。
这种情况当然与我们都害怕被讨厌,以及我们有多少放手有关逃避它。我与人建立了完整的关系,只是为了避免拒绝他们的尴尬。我做了你不应该做的事情:说是,后悔,回来说不,遇到阻力,吓坏了,说“其实,别担心,没关系”。这带来了最糟糕的结果:没有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同时看起来像个摇摇晃晃的混蛋。
如果我现在觉得自己超越了那个,陪审团仍然出去。但早期迹象是好的,可能部分是因为大流行。在两年没有经常旅行或外出之后,我们中的许多人对邀请和机会的反应与以前不同。期望发生了变化。计划已经改变。我们都习惯了沮丧和失望。在那里的某个地方,说“不”变得更容易了。鉴于所有这些,现在是重置硬边界的好时机。
我怀疑我愿意做看似困难的事情并不是年龄的函数。我没有时间或精力去建立关于别人讨厌我的奢侈幻想。我们假设别人比我们更脆弱;一次失望就会打破他们。我们也高估了我们每个人在他人想象中的位置,甚至在我们亲密的朋友和家人中。人有生命。他们和我们一样痴迷于自己。不参加朋友的婚礼,因为这意味着错过更大的优先事项,这是一个完全合理的决定。如果新娘不高兴,她会克服的。
所以这是我的新奇之处:在你说或做你害怕做的事情之前,你必须先坐下来辐射的不适。你必须尊重对方生气的权利,承认它是你行为的代价,并假设它会比你对它的怪异焦虑快得多。你必须相信结果——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你认为这是最好的——值得一些不适。很好。
我让我的孩子们退出了夏令营。组织者把我吓坏了。没有人死亡。你去吧。我今年 46 岁,最后——终于——想到“但如果他们生我的气怎么办?”可能会停止在我的决策中考虑这么多因素。
What's Your Rea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