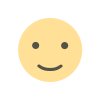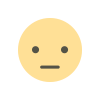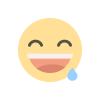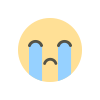Jing Tsu:“如果你研究中国,靠扶手椅奖学金的日子已经结束了”
当我遇到景祖时,我提出了一个紧迫的问题:在权力斗争中,文化理解的作用是什么?
Tsu 是讨论它的理想午餐伙伴:作为一位为英语观众解释和解释这个国家的美籍华裔文学学者,她形容自己是“坐在风暴眼中”。 . “如果你研究中国,靠纸上谈兵奖学金的日子已经结束。在这样一个极端两极分化的时代,我们负担不起这样做,”她补充道。
在她任教的耶鲁大学开始一系列公开演讲的最近一段视频中,Tsu 描述了关于中国的三种陈词滥调:“伟大的中国、糟糕的中国、疯狂的中国”。 “这就是我们需要改变的地方,以真正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她说,并补充说,这些故事“让中国感觉自己与众不同,而不仅仅是另一个试图原地踏步的新兴大国。”。
在中国报道六年后回到英国,我和 Tsu 一样,对我在西方遇到的中国政府的误解感到沮丧,比如它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它通常在内部孤立且不协调)。但我也对我的许多中国亲戚和同龄人看待西方的方式感到沮丧,而且我对中国对记者的日益狂热的攻击感到震惊。
当我走进位于伦敦市中心斯特兰德附近的一家通风良好的地中海餐厅 Toklas 时,我希望能遇到志趣相投的人。 Tsu 身着优雅的白色拉链夹克和粉蓝色上衣,以天生观察者的冷静站在桌子旁。当我们坐下时,在我提到习近平或乔·拜登之前,她问了第一个问题:“那你的故事是什么?”
我被陌生人问过无数次类似的问题,他们希望得到片面的解释。但在两个移民之间,问题是分享的邀请。我告诉她我的故事(来自中国大陆的父母移居英国接受高等教育,带我带着一个四岁的孩子)因为我知道她会告诉我她的故事。
Jing Tsu出生在台湾,据她自己的描述,她是一个“糟糕”的学生。她在 70 年代后期上小学,当时台湾仍处于 1949 年内战失败后逃离大陆的国民党政府的戒严令之下。
她和她的同学们不得不把头发从中间分开,剪到耳垂以下不到 2 厘米的地方,不能打耳洞。 Tsu 无视严格的制服规定,拒绝做作业,宁愿下课后往外跑。惩罚并没有打扰她。 “我是个假小子。老师们认为我没有羞耻感或屈辱感。他们称我为‘雌虎’,”她回忆道。
Tsu 的母亲 Sue 很担心她叛逆的女儿。 1983 年,苏九岁时,苏带着孩子去了美国,他们定居在新墨西哥州的一个小镇上。苏来到这里时不会说英语,也没有什么钱,她以单身母亲的身份抚养孩子——祖的父亲留在台湾。她将他们与社区的其他人分开:她不希望他们变得过于美国化。
苏曾是一名教师,她为她的孩子设计了一个“实验性”课程,用中文教授诗歌、书法和作文。每个星期天,她都会开车带他们三个半小时到最近的城镇阿尔伯克基上钢琴课。
“我们真的是一起长大的,”Tsu 谈到她自己和她的母亲时说;他们同时发现了美国社会。
当我建议我们看菜单时,我们无缝地转述了半个小时的故事。
我们点了开胃菜:菊苣沙拉、咸杏仁、柠檬腌凤尾鱼、Culaccia 火腿条。当他们来的时候,我们分享他们。我想一想我的祖父母会如何看待典型的伦敦餐:你移民到西部,努力工作,却在每个人都吃一道菜的餐馆里被敲诈了?一顿中餐是以菜的数量来衡量的,这都是共享的。
虽然这只是我对中国人的体验; Tsu 跟随散居在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的中国侨民的语言和文学。 “你可以无休止地争论什么是中国人。但它确实是一个兔子洞。它和世界人口一样多样化,”她说。
Tsu 说她选择文学领域“是因为它可以让你在幕后接触到你想知道的一切,而无需承担记者或社会科学家的责任。”他的方法使他能够涵盖广泛的学科,尤其是政治和历史。他最近的书,Kingdom of Characters,作为...

当我遇到景祖时,我提出了一个紧迫的问题:在权力斗争中,文化理解的作用是什么?
Tsu 是讨论它的理想午餐伙伴:作为一位为英语观众解释和解释这个国家的美籍华裔文学学者,她形容自己是“坐在风暴眼中”。 . “如果你研究中国,靠纸上谈兵奖学金的日子已经结束。在这样一个极端两极分化的时代,我们负担不起这样做,”她补充道。
在她任教的耶鲁大学开始一系列公开演讲的最近一段视频中,Tsu 描述了关于中国的三种陈词滥调:“伟大的中国、糟糕的中国、疯狂的中国”。 “这就是我们需要改变的地方,以真正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她说,并补充说,这些故事“让中国感觉自己与众不同,而不仅仅是另一个试图原地踏步的新兴大国。”。
在中国报道六年后回到英国,我和 Tsu 一样,对我在西方遇到的中国政府的误解感到沮丧,比如它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它通常在内部孤立且不协调)。但我也对我的许多中国亲戚和同龄人看待西方的方式感到沮丧,而且我对中国对记者的日益狂热的攻击感到震惊。
当我走进位于伦敦市中心斯特兰德附近的一家通风良好的地中海餐厅 Toklas 时,我希望能遇到志趣相投的人。 Tsu 身着优雅的白色拉链夹克和粉蓝色上衣,以天生观察者的冷静站在桌子旁。当我们坐下时,在我提到习近平或乔·拜登之前,她问了第一个问题:“那你的故事是什么?”
我被陌生人问过无数次类似的问题,他们希望得到片面的解释。但在两个移民之间,问题是分享的邀请。我告诉她我的故事(来自中国大陆的父母移居英国接受高等教育,带我带着一个四岁的孩子)因为我知道她会告诉我她的故事。
Jing Tsu出生在台湾,据她自己的描述,她是一个“糟糕”的学生。她在 70 年代后期上小学,当时台湾仍处于 1949 年内战失败后逃离大陆的国民党政府的戒严令之下。
她和她的同学们不得不把头发从中间分开,剪到耳垂以下不到 2 厘米的地方,不能打耳洞。 Tsu 无视严格的制服规定,拒绝做作业,宁愿下课后往外跑。惩罚并没有打扰她。 “我是个假小子。老师们认为我没有羞耻感或屈辱感。他们称我为‘雌虎’,”她回忆道。
Tsu 的母亲 Sue 很担心她叛逆的女儿。 1983 年,苏九岁时,苏带着孩子去了美国,他们定居在新墨西哥州的一个小镇上。苏来到这里时不会说英语,也没有什么钱,她以单身母亲的身份抚养孩子——祖的父亲留在台湾。她将他们与社区的其他人分开:她不希望他们变得过于美国化。
苏曾是一名教师,她为她的孩子设计了一个“实验性”课程,用中文教授诗歌、书法和作文。每个星期天,她都会开车带他们三个半小时到最近的城镇阿尔伯克基上钢琴课。
“我们真的是一起长大的,”Tsu 谈到她自己和她的母亲时说;他们同时发现了美国社会。
当我建议我们看菜单时,我们无缝地转述了半个小时的故事。
我们点了开胃菜:菊苣沙拉、咸杏仁、柠檬腌凤尾鱼、Culaccia 火腿条。当他们来的时候,我们分享他们。我想一想我的祖父母会如何看待典型的伦敦餐:你移民到西部,努力工作,却在每个人都吃一道菜的餐馆里被敲诈了?一顿中餐是以菜的数量来衡量的,这都是共享的。
虽然这只是我对中国人的体验; Tsu 跟随散居在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的中国侨民的语言和文学。 “你可以无休止地争论什么是中国人。但它确实是一个兔子洞。它和世界人口一样多样化,”她说。
Tsu 说她选择文学领域“是因为它可以让你在幕后接触到你想知道的一切,而无需承担记者或社会科学家的责任。”他的方法使他能够涵盖广泛的学科,尤其是政治和历史。他最近的书,Kingdom of Characters,作为...
What's Your Rea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