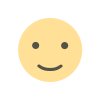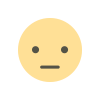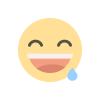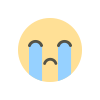我的孩子搬走了,但请不要说它是空巢
我几乎是一个空巢。它让人联想到流行文化中相互矛盾的形象:是编织和巡航,还是离婚和微剂量?无论哪种方式,都有一种自由的概念:学习陶瓷,成为一名酵母铰刀,从开放大学毕业,或者,就像我合唱团中的一个女人显然所做的那样,站在花园里大喊大叫。
关于大喊:我还没有觉得有必要。我一直很喜欢我的儿子们朝着自主的方向发展。这并不完全是自私的(尽管我迫不及待地想靠吐司和外卖过活)。我后来的童年记忆是无能为力的无聊;等待现实生活的开始。
无论如何,我的巢穴现在似乎并不空。你只需要数一数房子周围标有“PhD Nutrition”的超大塑料杯的数量(这些杯子是从哪里获得博士学位的,嗯)。它们坐在水槽里或沙发下,被一英寸的泥豌豆蛋白堵住了,蚂蚁们享受着改善肌肉张力的机会。我可以写一首厌恶蛋白质文化的赞美诗,假香草的酸辣味和对“散装”的崇拜,男子气概的字体和金属振动器球在滴水盘中纠缠并从橱柜中弹起,但会留到另一个时间。电视播放关于毒品交易的重磅剧,被遗弃的大教练伏击了患有关节炎的狗,我的硬皮藏品被洗劫一空,他们的父亲带着熟悉的徒劳咕哝着关于灯亮着的熟悉的徒劳。
尽管,当您阅读本文时,最小的孩子的成绩应该达到 A 级(我说“应该”,因为本周我在 Twitter 上看到一位老师问,很困惑,是否有人刚刚通过考试联系董事会想知道他们是否有时间纠正 A-level 试卷。我相信这很好!)。他会离开——老大已经离开了,只是路过——我们的巢穴将正式空了。
不过我想挑战那个巢穴的比喻。我猜人们开始考虑用鸟来养育孩子,因为我们已经看到羽毛版本年复一年地上演,它的大戏。但是作为一个在这个春天和夏天过着痴迷地观察我当地鸟类的人,这绝对不是一种补偿性应对策略——不,你为什么要这么说——我有笔记。
首先,鸟类世界中的死亡人数更多。我最小的儿子出门很晚,通常骑自行车,有时通宵达旦,有时毫无征兆。我醒着躺在床上,但他总是回来,直到现在。花园里的鸟儿就没那么幸运了:设法飞走的婴儿的百分比从来没有很高。三月,我打扰了他的评论,向他展示了一只黑鸟,他在窗外的树篱上拿着棍子和棉绒。四月份我看到她带来了虫咬,然后我看到她害怕地盘旋,因为邻居的猫在巢上方的栅栏上坐了几个小时,散发着随意的威胁(我把他赶走了,但他又回来了),然后我没看到她。我把死去的婴儿从巢里拉出来,半毛、虫眼、瘦弱,哭了好几天。一只小麻雀飞进窗户,摔断了脖子;一只年轻的普通八哥死于断肢。
养育我们的孩子的过程也慢得多。当然,我们的寿命要长得多,但我看着大山雀照料它们尖叫婴儿的巢箱的那几周感觉就像成人和年轻人生存的疯狂斗争。也许我离新生儿的生活太远了,以至于我不记得那种感觉了,但是养育人类是一场马拉松:吃饭、洗衣服和学习;失败和错误;只是偶尔把它弄好。
然后当小鸟离开时,它就是最终的。直到六月,我儿子早上带着他的装有钢笔的透明塑料袋去骑自行车,而我则通过填充喂食器和水碗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我听着现在熟悉的拼凑的电话——警报、安慰和录音——就像我的“那怎么样?” WhatsApps 尚未阅读。然后考试结束,他消失在漫长的夏日派对和告别中。鸟也。前花园里的黑鹂,最终成功地繁衍了一窝,一夜之间消失了。十几岁的大山雀已经在树篱里争吵了几个星期,但现在它们也散了。就连那些花了数周时间心满意足地划过水碗的没有喉咙的幼鸽也不见了。但是我的儿子回来了,筋疲力尽,宿醉(我的另一个儿子已经回家以蚱蜢效率剥离橱柜)。年轻人不再真的离开家了,在这个经济体中更是如此。鸟是严肃的。
好吧,除非你是亚历克·鲍德温或伯尼·埃克莱斯顿,否则就是这样:不会再有后代了。所以感谢上帝的鸟,这似乎是我的空巢爱好,而不是死藤水或秋千。底部有长尾山雀的山雀...

我几乎是一个空巢。它让人联想到流行文化中相互矛盾的形象:是编织和巡航,还是离婚和微剂量?无论哪种方式,都有一种自由的概念:学习陶瓷,成为一名酵母铰刀,从开放大学毕业,或者,就像我合唱团中的一个女人显然所做的那样,站在花园里大喊大叫。
关于大喊:我还没有觉得有必要。我一直很喜欢我的儿子们朝着自主的方向发展。这并不完全是自私的(尽管我迫不及待地想靠吐司和外卖过活)。我后来的童年记忆是无能为力的无聊;等待现实生活的开始。
无论如何,我的巢穴现在似乎并不空。你只需要数一数房子周围标有“PhD Nutrition”的超大塑料杯的数量(这些杯子是从哪里获得博士学位的,嗯)。它们坐在水槽里或沙发下,被一英寸的泥豌豆蛋白堵住了,蚂蚁们享受着改善肌肉张力的机会。我可以写一首厌恶蛋白质文化的赞美诗,假香草的酸辣味和对“散装”的崇拜,男子气概的字体和金属振动器球在滴水盘中纠缠并从橱柜中弹起,但会留到另一个时间。电视播放关于毒品交易的重磅剧,被遗弃的大教练伏击了患有关节炎的狗,我的硬皮藏品被洗劫一空,他们的父亲带着熟悉的徒劳咕哝着关于灯亮着的熟悉的徒劳。
尽管,当您阅读本文时,最小的孩子的成绩应该达到 A 级(我说“应该”,因为本周我在 Twitter 上看到一位老师问,很困惑,是否有人刚刚通过考试联系董事会想知道他们是否有时间纠正 A-level 试卷。我相信这很好!)。他会离开——老大已经离开了,只是路过——我们的巢穴将正式空了。
不过我想挑战那个巢穴的比喻。我猜人们开始考虑用鸟来养育孩子,因为我们已经看到羽毛版本年复一年地上演,它的大戏。但是作为一个在这个春天和夏天过着痴迷地观察我当地鸟类的人,这绝对不是一种补偿性应对策略——不,你为什么要这么说——我有笔记。
首先,鸟类世界中的死亡人数更多。我最小的儿子出门很晚,通常骑自行车,有时通宵达旦,有时毫无征兆。我醒着躺在床上,但他总是回来,直到现在。花园里的鸟儿就没那么幸运了:设法飞走的婴儿的百分比从来没有很高。三月,我打扰了他的评论,向他展示了一只黑鸟,他在窗外的树篱上拿着棍子和棉绒。四月份我看到她带来了虫咬,然后我看到她害怕地盘旋,因为邻居的猫在巢上方的栅栏上坐了几个小时,散发着随意的威胁(我把他赶走了,但他又回来了),然后我没看到她。我把死去的婴儿从巢里拉出来,半毛、虫眼、瘦弱,哭了好几天。一只小麻雀飞进窗户,摔断了脖子;一只年轻的普通八哥死于断肢。
养育我们的孩子的过程也慢得多。当然,我们的寿命要长得多,但我看着大山雀照料它们尖叫婴儿的巢箱的那几周感觉就像成人和年轻人生存的疯狂斗争。也许我离新生儿的生活太远了,以至于我不记得那种感觉了,但是养育人类是一场马拉松:吃饭、洗衣服和学习;失败和错误;只是偶尔把它弄好。
然后当小鸟离开时,它就是最终的。直到六月,我儿子早上带着他的装有钢笔的透明塑料袋去骑自行车,而我则通过填充喂食器和水碗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我听着现在熟悉的拼凑的电话——警报、安慰和录音——就像我的“那怎么样?” WhatsApps 尚未阅读。然后考试结束,他消失在漫长的夏日派对和告别中。鸟也。前花园里的黑鹂,最终成功地繁衍了一窝,一夜之间消失了。十几岁的大山雀已经在树篱里争吵了几个星期,但现在它们也散了。就连那些花了数周时间心满意足地划过水碗的没有喉咙的幼鸽也不见了。但是我的儿子回来了,筋疲力尽,宿醉(我的另一个儿子已经回家以蚱蜢效率剥离橱柜)。年轻人不再真的离开家了,在这个经济体中更是如此。鸟是严肃的。
好吧,除非你是亚历克·鲍德温或伯尼·埃克莱斯顿,否则就是这样:不会再有后代了。所以感谢上帝的鸟,这似乎是我的空巢爱好,而不是死藤水或秋千。底部有长尾山雀的山雀...
What's Your Rea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