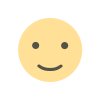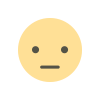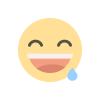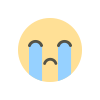有些菜会永远伴随着你。我应该再找他们吗? |雷切尔库克
每年的这个时候,很容易将这样的空间用于制定和打破厨房决议(我拒绝说节食这个词)。但我会笨手笨脚,把所有这些都留到下个月。一月已经够糟了,更不用说腰围了。换个好消息怎么样,比如深受喜爱且才华横溢的主厨 Henry Harris 在圣诞节前不久悄悄开了他的新餐厅 Bouchon Racine?
听着,我可以,我不会世界上只有我会永远记住至少六种菜肴,这些菜肴在当时都非常美味——结合了各种环境和如此多的食材——它们肯定会在我的余生。就像我吃的螃蟹三明治永远不会像我在诺森伯兰郡的一家 Seahouses 酒吧里在肮脏的天气里长途跋涉后吃的那样好吃,没有任何烤鸡配米饭和西红柿能比得上那些淋湿我的人(我曾经)在土耳其湖中央的一艘旧船上游过。我吃knafeh,每当我看到它时都会滴糖浆和软奶酪。但我从来没有尝过像 2005 年我在拉马拉糖果店的荧光条下贪婪地啜饮的那片美味,这是我几天辛勤工作的回报。
但它是人性想要尝试复制完美,尽管我们很清楚这不可避免地只会导致失望。当我听说哈里斯在 Clerkenwell 的一家酒吧楼上开了一家餐厅时,我满脑子想的就是他最初在骑士桥的拉辛餐厅供应的藏红花和大蒜慕斯配贻贝。它会在菜单上吗?如果确实如此,它还会很棒吗?我很少去拉辛——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错误的城镇,不止一个——但每次,我吃的都是这个慕斯,由正在服用的好朋友推动,他和我一样爱.拉辛八年前关门了,成为租金上涨的受害者,但我从未忘记这种泡沫的奶油味和微妙感,它迅速消失的轻松显然对更慢地吃它的能力没有影响。
所以我在圣诞节和元旦之间安静的日子里在 Bouchon Racine 订了一张桌子时有些忐忑不安,也许当黑板上的黑板出现时我暗自松了一口气菜单上写的没有提到这个著名的慕斯。我吃了一份完美无暇的沙拉(蜗牛配龙蒿和鲜橙米莫莱特刨花),然后是兔子配芥末酱和焦糖焦糖,一切都很顺利。但是,我就是忍不住。当我们的服务员慷慨地将致命的老西梅倒进两个杯子时——我真的不应该喝它,但我喝了,所以开枪吧——我问某个条目是否会在适当的时候重新流行起来。
不确定我在等待答案;当他消失时,我预料到账单并喃喃地说“也许吧”。但随着事情的发展,我从哈里斯本人那里得到了一个回应,我的意思是,他立即出现在我们的餐桌旁。根据我的记忆(我有点醉了),他说他仍在考虑他真正应该把哪些他最喜欢的东西放在菜单上——兔子显然是个饲养员——但是,是的,苔藓可能会重新出现在菜单上一些点。然后他自嘲地开了个玩笑,说他的拿手好戏是做适合没有牙齿的人的菜(也许他知道我吃的是焦糖焦糖)。
就我而言,我有点尴尬。我不想让他认为我的晚餐以任何方式失败了,因为这是天堂般的,完全不可能改进。但我也突然有了一种越来越强烈的希望,尽管我已经吃饱了,几乎无法动弹。圣杯!摇摇晃晃的黄色和非常苍白,它再次出现在视线中。当我回到家时,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预订另一张桌子。

每年的这个时候,很容易将这样的空间用于制定和打破厨房决议(我拒绝说节食这个词)。但我会笨手笨脚,把所有这些都留到下个月。一月已经够糟了,更不用说腰围了。换个好消息怎么样,比如深受喜爱且才华横溢的主厨 Henry Harris 在圣诞节前不久悄悄开了他的新餐厅 Bouchon Racine?
听着,我可以,我不会世界上只有我会永远记住至少六种菜肴,这些菜肴在当时都非常美味——结合了各种环境和如此多的食材——它们肯定会在我的余生。就像我吃的螃蟹三明治永远不会像我在诺森伯兰郡的一家 Seahouses 酒吧里在肮脏的天气里长途跋涉后吃的那样好吃,没有任何烤鸡配米饭和西红柿能比得上那些淋湿我的人(我曾经)在土耳其湖中央的一艘旧船上游过。我吃knafeh,每当我看到它时都会滴糖浆和软奶酪。但我从来没有尝过像 2005 年我在拉马拉糖果店的荧光条下贪婪地啜饮的那片美味,这是我几天辛勤工作的回报。
但它是人性想要尝试复制完美,尽管我们很清楚这不可避免地只会导致失望。当我听说哈里斯在 Clerkenwell 的一家酒吧楼上开了一家餐厅时,我满脑子想的就是他最初在骑士桥的拉辛餐厅供应的藏红花和大蒜慕斯配贻贝。它会在菜单上吗?如果确实如此,它还会很棒吗?我很少去拉辛——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错误的城镇,不止一个——但每次,我吃的都是这个慕斯,由正在服用的好朋友推动,他和我一样爱.拉辛八年前关门了,成为租金上涨的受害者,但我从未忘记这种泡沫的奶油味和微妙感,它迅速消失的轻松显然对更慢地吃它的能力没有影响。
所以我在圣诞节和元旦之间安静的日子里在 Bouchon Racine 订了一张桌子时有些忐忑不安,也许当黑板上的黑板出现时我暗自松了一口气菜单上写的没有提到这个著名的慕斯。我吃了一份完美无暇的沙拉(蜗牛配龙蒿和鲜橙米莫莱特刨花),然后是兔子配芥末酱和焦糖焦糖,一切都很顺利。但是,我就是忍不住。当我们的服务员慷慨地将致命的老西梅倒进两个杯子时——我真的不应该喝它,但我喝了,所以开枪吧——我问某个条目是否会在适当的时候重新流行起来。
不确定我在等待答案;当他消失时,我预料到账单并喃喃地说“也许吧”。但随着事情的发展,我从哈里斯本人那里得到了一个回应,我的意思是,他立即出现在我们的餐桌旁。根据我的记忆(我有点醉了),他说他仍在考虑他真正应该把哪些他最喜欢的东西放在菜单上——兔子显然是个饲养员——但是,是的,苔藓可能会重新出现在菜单上一些点。然后他自嘲地开了个玩笑,说他的拿手好戏是做适合没有牙齿的人的菜(也许他知道我吃的是焦糖焦糖)。
就我而言,我有点尴尬。我不想让他认为我的晚餐以任何方式失败了,因为这是天堂般的,完全不可能改进。但我也突然有了一种越来越强烈的希望,尽管我已经吃饱了,几乎无法动弹。圣杯!摇摇晃晃的黄色和非常苍白,它再次出现在视线中。当我回到家时,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预订另一张桌子。
What's Your Rea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