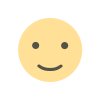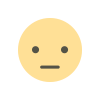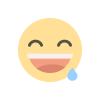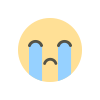一个改变我的时刻:我以为我会在加拿大找到天堂——结果却遇到了一个叫我阿拉丁的醉汉
守卫的名字叫迈克尔,在黎巴嫩阿拉伯语中读作米歇尔。 2014 年的那一天,当我最后一次离开贝鲁特时,他在哈里里机场高速公路上的军事检查站拦住了我们的车。 “你为什么要去机场?”迈克尔一边检查我的叙利亚护照,一边问道,翻页速度太快以至于无法阅读。他的 M16 步枪搁在他的肩上。他的军装从来没有碰过铁。
“我要移民加拿大,”我回答。我的话似乎让他生气了。他翻阅了这些页面,直到找到了加拿大签证。他等了一会儿,然后把护照扔出车窗。他落在我的腿上。
“你这该死的难民,”他喊道。 “你们叙利亚人,来黎巴嫩,吃我们的食物,接受我们的工作,然后飞往一个豪华的国家。”
我保持沉默。我不打算和一个武装少年争论。我正在开车的黎巴嫩朋友在座位上不舒服地动了动。
“去你的应许之地!”
几个小时后,我坐在拥挤的飞机上,前往那片应许之地。我的生活正在改变,我还不知道。在接下来的九个月里,作为移民的压力会降临到我身上。我会减掉超过四分之一的体重,用大麻、酒和派对药物来治疗,最终会崩溃并精疲力尽。
但它正在向前发展。
我对我在加拿大的生活有一个很好的想法,虽然很天真。在黎巴嫩做了两年的酷儿叙利亚难民后,我认为一切都会水到渠成。西方常见的奇怪快乐的画面充满了我的脑海:骄傲游行;男孩们在可爱的咖啡馆里手捧热饮。我是通过一项名为“私人赞助难民计划”的加拿大特定倡议获得赞助的:一群加拿大公民,其中大多数是老年白人男子,联手向他们的政府提交申请,要求将我安全运送到加拿大。我以为我会立即受到爱戴和保护 - 并最终安全。
这与事实相去甚远。我有时会开玩笑说,我在加拿大的第一年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一年——但这并不是开玩笑。
我的假设与 Michael 的假设相似,the黎巴嫩卫队。我相信,在摆脱了中东恐同的束缚之后,我会在这片有奶有蜜的土地上受到欢迎,大门会敞开。我会成为我一直想成为的作家。我将拥有我一直梦想的肆无忌惮的酷儿生活。回想起来,这很愚蠢——就像我期待一个有合同的经纪人在机场等我一样,还有一队可爱的男孩带我去浪漫约会。
看来,创伤不是你可以在贝鲁特机场留下的东西。当我到达加拿大时,我带来了自己的创伤经历清单。他们被隐藏起来,就像在浑水中睡觉的鳄鱼:被遗弃和拒绝的复杂家族史,由于我的性取向而多年生活在恐惧中,由于我在 LGBTQ+ 社区的积极行动而被叙利亚当局短暂逮捕,以及两个在黎巴嫩作为难民生活了多年 - 被同性恋恐惧症、仇外心理和被送回我国内战地区的可能性所包围。
我记得第一次醒来在加拿大。我坐在清晨的黑暗中,摆脱时差,倾听。很安静:外面没有声音。没有爆炸或喇叭。没有人们喊叫或警笛的旋律。
出于某种原因,这种沉默让我害怕。
归属感,我很快就发现了,不是您在新家门口收到的礼物。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一直在努力寻找一个朋友社区。了解我加入的这个社会的社会地标;找到一份符合我愿望的工作。
最重要的是,我必须学会驾驭一个对我来说很新的概念:种族主义。我在叙利亚占主导地位的种族认同中长大,直到我搬到加拿大并成为少数族裔,我才意识到这是我的特权。再加上我带有口音的英语和难民背景,我被微攻击、就业市场前景的局限、对我性格的假设以及最糟糕的是怜悯所淹没。/p>
“你是阿拉丁吗?”
“打扰一下?”
“你是阿拉丁吗?”他在 DJ 的音乐中大喊。
“阿拉丁是一个虚构人物。”
“嗯。”他抓住我的肩膀,把我的脖子拉向他:“亲我一下,你在逃跑……

守卫的名字叫迈克尔,在黎巴嫩阿拉伯语中读作米歇尔。 2014 年的那一天,当我最后一次离开贝鲁特时,他在哈里里机场高速公路上的军事检查站拦住了我们的车。 “你为什么要去机场?”迈克尔一边检查我的叙利亚护照,一边问道,翻页速度太快以至于无法阅读。他的 M16 步枪搁在他的肩上。他的军装从来没有碰过铁。
“我要移民加拿大,”我回答。我的话似乎让他生气了。他翻阅了这些页面,直到找到了加拿大签证。他等了一会儿,然后把护照扔出车窗。他落在我的腿上。
“你这该死的难民,”他喊道。 “你们叙利亚人,来黎巴嫩,吃我们的食物,接受我们的工作,然后飞往一个豪华的国家。”
我保持沉默。我不打算和一个武装少年争论。我正在开车的黎巴嫩朋友在座位上不舒服地动了动。
“去你的应许之地!”
几个小时后,我坐在拥挤的飞机上,前往那片应许之地。我的生活正在改变,我还不知道。在接下来的九个月里,作为移民的压力会降临到我身上。我会减掉超过四分之一的体重,用大麻、酒和派对药物来治疗,最终会崩溃并精疲力尽。
但它正在向前发展。
我对我在加拿大的生活有一个很好的想法,虽然很天真。在黎巴嫩做了两年的酷儿叙利亚难民后,我认为一切都会水到渠成。西方常见的奇怪快乐的画面充满了我的脑海:骄傲游行;男孩们在可爱的咖啡馆里手捧热饮。我是通过一项名为“私人赞助难民计划”的加拿大特定倡议获得赞助的:一群加拿大公民,其中大多数是老年白人男子,联手向他们的政府提交申请,要求将我安全运送到加拿大。我以为我会立即受到爱戴和保护 - 并最终安全。
这与事实相去甚远。我有时会开玩笑说,我在加拿大的第一年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一年——但这并不是开玩笑。
我的假设与 Michael 的假设相似,the黎巴嫩卫队。我相信,在摆脱了中东恐同的束缚之后,我会在这片有奶有蜜的土地上受到欢迎,大门会敞开。我会成为我一直想成为的作家。我将拥有我一直梦想的肆无忌惮的酷儿生活。回想起来,这很愚蠢——就像我期待一个有合同的经纪人在机场等我一样,还有一队可爱的男孩带我去浪漫约会。
看来,创伤不是你可以在贝鲁特机场留下的东西。当我到达加拿大时,我带来了自己的创伤经历清单。他们被隐藏起来,就像在浑水中睡觉的鳄鱼:被遗弃和拒绝的复杂家族史,由于我的性取向而多年生活在恐惧中,由于我在 LGBTQ+ 社区的积极行动而被叙利亚当局短暂逮捕,以及两个在黎巴嫩作为难民生活了多年 - 被同性恋恐惧症、仇外心理和被送回我国内战地区的可能性所包围。
我记得第一次醒来在加拿大。我坐在清晨的黑暗中,摆脱时差,倾听。很安静:外面没有声音。没有爆炸或喇叭。没有人们喊叫或警笛的旋律。
出于某种原因,这种沉默让我害怕。
归属感,我很快就发现了,不是您在新家门口收到的礼物。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一直在努力寻找一个朋友社区。了解我加入的这个社会的社会地标;找到一份符合我愿望的工作。
最重要的是,我必须学会驾驭一个对我来说很新的概念:种族主义。我在叙利亚占主导地位的种族认同中长大,直到我搬到加拿大并成为少数族裔,我才意识到这是我的特权。再加上我带有口音的英语和难民背景,我被微攻击、就业市场前景的局限、对我性格的假设以及最糟糕的是怜悯所淹没。/p>
“你是阿拉丁吗?”
“打扰一下?”
“你是阿拉丁吗?”他在 DJ 的音乐中大喊。
“阿拉丁是一个虚构人物。”
“嗯。”他抓住我的肩膀,把我的脖子拉向他:“亲我一下,你在逃跑……
What's Your Rea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