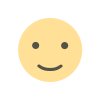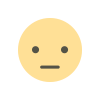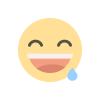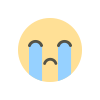奶奶刚刚去世,我离家出走。然后我喝了——疼痛消失了 |阿德里安·奇利斯
这一切都是关于第一杯酒,就像你生命中的第一杯酒和一天中的第一杯酒。这就是我在写一本关于减少酒精的书时学到的东西,这本书首先要了解我是如何喝得这么多的。我可以追溯到我 14 岁时在德国度过的一个悲惨的两周。
那是一次学校交流。我和一个男孩配对,我会叫 Siegfried。我们没有任何共同点。这完全是我的错,因为在我们填写兴趣表的那一周内,我就开始下棋了。我已经正式宣布,国际象棋是我生活中的主要兴趣。此情况并非如此。我的主要兴趣是足球、音乐和一连串女孩的单相崇拜。我很快意识到我棋不好,放弃了,但此时媒人选择机器的轮子正在转动。不需要特别彻底地运用条顿人的逻辑,我就可以将我与德国学校国际象棋冠军配对。
可怜的齐格弗里德看起来就像学校国际象棋选手的每一寸。他戴着那种能让眼睛变大的眼镜。我也戴眼镜,近视,所以我想我们有一些共同点,但仅此而已。
对我来说,整个旅程在开始前一天就崩溃了.当我放学回家时,我最强烈的感觉是有什么不对劲。不久之后,我父亲告诉我,我在克罗地亚的祖母病得很重。巴卡,正如我所说的那样,在她位于萨格勒布的家中中风了。我妈妈正在和她姐姐通电话。我离我的巴卡很近;她和我们一起度过了每个圣诞节。我真的不想参加愚蠢的德国交流。我非常沮丧和焦虑,从我和齐格弗里德的通信中已经清楚地表明他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但是爸爸妈妈决定我必须去.我真希望他们没有。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悲惨过;想想看,从那以后我就没有这么难过了。对任何人来说,从来没有过如此缓慢的两周。这所学校位于斯图加特附近的莱昂贝格镇。我和齐格弗里德相处得和我担心的一样糟糕。我渴望地看着我的同学们,他们都和他们的新朋友一起度过了美好的时光。德国女孩非常漂亮,显然对我或我戴眼镜的同事不感兴趣。我们一言不发地回家了。令他惊讶的是,我拒绝了他所有关于下棋的提议。最终我屈服了,只是为了向他展示我是多么的无知,这并没有花费很长时间。我们不再下棋了。
我非常想家,身体受到了伤害。更糟糕的是,我到达后几天,我妈妈打电话来了。她说:“萨格勒布的情况没有改变,我们明天要去那里。”萨格勒布局势不变?这听起来像是新闻主播可能会说的话。我妈妈只是没有那样说话。我知道我的 Baka 已经死了。
我跌得更低了。齐格弗里德的母亲是个可爱的女人,她想尽一切办法让我振作起来,但没有成功。家里的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一份关于我队最好的球员布莱恩·罗布森被卖给曼联的剪报。如果有可能死于纯粹的不幸,那将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让我看到我最后一口气。
我几乎没有记忆我们交流团参加的短途旅行中,除了一次。第二周,我们参加了 Leonberg 啤酒厂之旅。我踩着轻便摩托车,不喜欢这种气味,当我们看到啤酒是如何制作的时,我茫然地凝视着。在旅行结束时,我们坐在长桌旁,喝了可能相当浓烈的啤酒。我不太喜欢它,但在它流过我的血管的几分钟内,我经历了某种情感转变。
真是太好了。在那一点上,我们留在交易所的最后几天从感觉像是永恒变成了朦胧和微不足道的东西,甚至可能是愉快的。我和朋友们开怀大笑,甚至以为我看到一个叫克劳迪娅的女孩盯着我看。我为可怜的齐格弗里德悲痛欲绝,他只喝了一口啤酒,却带着难以忍受的甜蜜,显然很高兴看到我微笑。
Waves幸福降临在我身上。这是在我生命的关键形成阶段的创伤时刻。我以前从未处理过亲人的死亡。我正在经历震惊、困惑、恐惧、孤独和可怕而令人心碎的乡愁。我生病了。但是,喝一口这种奇怪的啤酒就可以消除这种痛苦。几分钟之内,我的整个世界都被重构了。这很神奇。为什么我不想要更多相同的东西?
四十年后,哈...

这一切都是关于第一杯酒,就像你生命中的第一杯酒和一天中的第一杯酒。这就是我在写一本关于减少酒精的书时学到的东西,这本书首先要了解我是如何喝得这么多的。我可以追溯到我 14 岁时在德国度过的一个悲惨的两周。
那是一次学校交流。我和一个男孩配对,我会叫 Siegfried。我们没有任何共同点。这完全是我的错,因为在我们填写兴趣表的那一周内,我就开始下棋了。我已经正式宣布,国际象棋是我生活中的主要兴趣。此情况并非如此。我的主要兴趣是足球、音乐和一连串女孩的单相崇拜。我很快意识到我棋不好,放弃了,但此时媒人选择机器的轮子正在转动。不需要特别彻底地运用条顿人的逻辑,我就可以将我与德国学校国际象棋冠军配对。
可怜的齐格弗里德看起来就像学校国际象棋选手的每一寸。他戴着那种能让眼睛变大的眼镜。我也戴眼镜,近视,所以我想我们有一些共同点,但仅此而已。
对我来说,整个旅程在开始前一天就崩溃了.当我放学回家时,我最强烈的感觉是有什么不对劲。不久之后,我父亲告诉我,我在克罗地亚的祖母病得很重。巴卡,正如我所说的那样,在她位于萨格勒布的家中中风了。我妈妈正在和她姐姐通电话。我离我的巴卡很近;她和我们一起度过了每个圣诞节。我真的不想参加愚蠢的德国交流。我非常沮丧和焦虑,从我和齐格弗里德的通信中已经清楚地表明他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但是爸爸妈妈决定我必须去.我真希望他们没有。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悲惨过;想想看,从那以后我就没有这么难过了。对任何人来说,从来没有过如此缓慢的两周。这所学校位于斯图加特附近的莱昂贝格镇。我和齐格弗里德相处得和我担心的一样糟糕。我渴望地看着我的同学们,他们都和他们的新朋友一起度过了美好的时光。德国女孩非常漂亮,显然对我或我戴眼镜的同事不感兴趣。我们一言不发地回家了。令他惊讶的是,我拒绝了他所有关于下棋的提议。最终我屈服了,只是为了向他展示我是多么的无知,这并没有花费很长时间。我们不再下棋了。
我非常想家,身体受到了伤害。更糟糕的是,我到达后几天,我妈妈打电话来了。她说:“萨格勒布的情况没有改变,我们明天要去那里。”萨格勒布局势不变?这听起来像是新闻主播可能会说的话。我妈妈只是没有那样说话。我知道我的 Baka 已经死了。
我跌得更低了。齐格弗里德的母亲是个可爱的女人,她想尽一切办法让我振作起来,但没有成功。家里的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一份关于我队最好的球员布莱恩·罗布森被卖给曼联的剪报。如果有可能死于纯粹的不幸,那将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让我看到我最后一口气。
我几乎没有记忆我们交流团参加的短途旅行中,除了一次。第二周,我们参加了 Leonberg 啤酒厂之旅。我踩着轻便摩托车,不喜欢这种气味,当我们看到啤酒是如何制作的时,我茫然地凝视着。在旅行结束时,我们坐在长桌旁,喝了可能相当浓烈的啤酒。我不太喜欢它,但在它流过我的血管的几分钟内,我经历了某种情感转变。
真是太好了。在那一点上,我们留在交易所的最后几天从感觉像是永恒变成了朦胧和微不足道的东西,甚至可能是愉快的。我和朋友们开怀大笑,甚至以为我看到一个叫克劳迪娅的女孩盯着我看。我为可怜的齐格弗里德悲痛欲绝,他只喝了一口啤酒,却带着难以忍受的甜蜜,显然很高兴看到我微笑。
Waves幸福降临在我身上。这是在我生命的关键形成阶段的创伤时刻。我以前从未处理过亲人的死亡。我正在经历震惊、困惑、恐惧、孤独和可怕而令人心碎的乡愁。我生病了。但是,喝一口这种奇怪的啤酒就可以消除这种痛苦。几分钟之内,我的整个世界都被重构了。这很神奇。为什么我不想要更多相同的东西?
四十年后,哈...
What's Your Reaction?